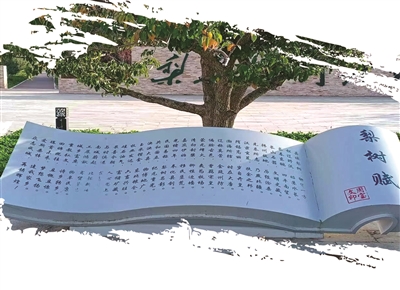| 黑土大地培根魂 ——周保文散文的山水吟诵 |
| ||
|
张伟/文
我和周保文结识很早,早到我还没向文学抛媚的时候。1984年我在梨树党校给成年人讲课,那些人大都是梨树县有身份没学历的人,国家给他们补学历的机会——成人高考。其中不乏一些各级别领导,周俭是外贸局局长。那会儿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又因为物品紧缺,需要有计划地配置,类似供销、商业、外贸等部门把持着物品分配份额,冰箱、电视、自行车、茅台、苹果等紧俏物品凭票采购,外贸局局长就显得比较重要,当然也是有权利地位的局长了。我虽站在讲台上授课,也仅仅是一名普通老师而已,何况那时我才20岁,所谓的“学生”大多已经在不惑和知天命之间。地位和年龄的反差,让我有一种本末倒置的错愕,甚至讲课也不敢高声,似麻雀在讲台上给众神表演,自然,授课效果不佳。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位外贸局长把他儿子介绍给我,他儿子就是周保文,当时在四平师院读书,还谦虚地警示周保文,小张老师古典文学底子深厚,你要好好向小张老师学习。就这样我认识了周保文。当然,自那以后,我的讲课效果也出来了,是周俭的谦虚,给我抬高了语音分贝。
周保文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梨树县行政部门工作,宣传部、县文联、机关党工委。梨树有两个文化坐标点,一个是二人转,一个是黑土地。梨树是我的故乡,故乡,只有离开方为故乡。我在1986年离开梨树投奔四平,周保文1986年大学毕业从四平回到梨树。周保文在1986年一头扎进梨树就在黑土地上扎根,尽管那时周保文还很年轻,有很多机会走进四平或者省城,外面的诸多诱惑并没有把周保文从黑土地上拽走。周保文的父亲周俭当过语文老师,大概是受其父亲的影响,周保文酷爱文字,尽管行政工作诸事缠身,也没有把周保文从文字身边拽走。周保文固守着梨树黑土大地,固守文字这片圣洁的天空。因为黑土地和文字,我们这两只青涩的瓜妞,通过黑土地上的一棵文字藤,一直连接着,直到现在。
周保文出版了五本个人散文集,《与谁共舞》《山水有约》《非常人物》《我行我述》《溪山入话》。
散文集《与谁共舞》“诗词撷英”,是一组阅读古典诗词的随笔性文字,包括《诗词与梅》《诗词与莲》《诗词与山》《诗词与月》等25个篇目。每个篇目下,将古典诗词中描写的某个特定意象的经典词句,用充满诗意的文字连缀起来,还原出当时特有的意境,并从中梳理出具有规律性的思想与情感,进而揭示这个意象在古典诗词中所特有的文化意蕴与象征。比如,在《诗词与梅》的结尾,这样写道:“对梅个性的挖掘与展示,说到底是诗人对自我个性的反省与表露。高洁的梅花,其实正是诗人清纯品格、清芬志趣、清净胸襟的写照。换句话说,诗人的爱花,也就是诗人的自爱。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诗人们为什么要‘瘦骞冲寒溪上去’悄悄地寻梅;为什么要‘闲来立断清风影’去静静地赏梅;为什么要‘为爱梅花月,终宵不肯眠’久久地伴梅;又为什么要追问着‘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苦苦地忆梅了——”事实上,对这些古典诗章词句的偏爱和积累,是与他早年大学的阅读经历密不可分的。也很可能,当年周俭先生把他介绍给我,说了句“小张老师的古典文学底子厚”让他受了刺激,毕竟“小张老师”是白城师专毕业,周保文读的是本科。
正如周保文在一次阅读对话中所说:“我的学习经历可以一直追溯到我的童年。我是在农村出生的孩子,可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小镇里长大。我感谢我的父亲,他的师范毕业出身、小学教师生涯、机关工作履历,都对我早期的教育和启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里就到处堆满了报刊和书籍。从被书刊上那些漂亮的插图所吸引,到对上面的文字感兴趣,一切关于文化的概念都在潜移默化中深入灵魂里。记得是小学五年级的夏天,我去外祖父家过暑假。燠热的天气,让我的内心感到烦躁而不安。恰在这时,无所事事的我,忽然在外祖父家的书架上发现了厚厚的《文学基础知识》(我的外祖父和我老姨都是老师)。不经意的甚至可能是闲极无聊时的这一次随手翻阅,最终竟让我与文字、与文学结下了一生难解难分的宿缘。自从第一次翻阅这本《文学基础知识》,整个暑假我就再也没有将它放下。我被这本书里所讲述的关于李白、杜甫、王勃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有些篇什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忽然意识到在现实的世界之外,原来还有一个如此美不胜收的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原来还有那么多如此引人入胜的奇妙故事。世界在我的面前,从此打开了另一道神奇的大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语文课本是政治性很强的,但其中的诸多名篇依然让我们拿到了那一枚通往文学堂奥的金色钥匙。巴金的《雷雨》、翦伯赞的《内蒙访古》——高中语文老师那娓娓的讲述,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是余音绕梁。”
真正的系统性学习文学,源自他的大学四年。1982年7月,周保文以超出重点大学录取线十几分的成绩,即将实现他报考的第一志愿——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然而命运的阴差阳错让他最终成为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学生中的一员。中文系的科班教育,让周保文从此与文学、与文字结下了职业之缘。为了弥补没有考上东北师大的遗憾,为了在另一片天地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以高中备考的劲头去学大学里的每一门课程。对学到的所有课程似乎都是那样的如饥似渴。知识的滋养是潜移默化和循序渐进的,但同时也是实实在在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你付出了多少精力,学业就会最终就会回报你多少进步与成长。
“大学二年级暑假,父亲把我引荐给一个大专毕业的党校老师,说了句小张老师古典文学底子厚。我父亲师范毕业,当然有他的眼光,甚至用不着去佐证,后来的交往也证明了我父亲的话不是假的,那位党校老师发表了很多文章,字里行间蕴藏着孔子的洁、老子的逸、庄子的空。从那以后我开始阅读古典文学,一本古典诗词伴随我在宿舍后面的果园里散步和晨读,而每一个夜晚又是图书馆的灯光把文学世界里的殿堂照亮。整个大学期间,我除了以优异的成绩完成所有的学业,还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其他书籍,记下几十本厚厚的读书笔记。幸运的是,正是在这里我喜欢上了诗歌并且开始写作,直到现在我依然为我的毕业论文《系统论之于当代诗歌》能够排在全校当年《优秀毕业论文选》的第一篇而骄傲——”
周保文的《山水有约》《我行我述》《溪山入话》都是这些年个人旅痕的记录。从对景物的客观描摹与复述,到从中升华出对人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与感悟,这是他的游记写作渐入佳境的一个明显标志,充满了人文精神的游记,才是更深层次的、有价值的文字。
周保文毕业后就在机关工作,最初肯定是机关应用文写作,机关工作的高屋建瓴,对社会万象的深刻洞察,对政策性书籍的职业性阅读,特别是对文化、哲学方面书籍的阅读,都对文学创作有重大裨益。
机关的应用文和文学作品,是两种方向完全不同的写作。应用文要求的是一字不虚、开门见山;文学作品崇尚的是文字贵曲、繁花锦绣。但道理是一样的,彼此是相通的。文学创作中较强的分析、归纳能力,文字的组织能力,同样适用于机关应用文。有了文学创作的功底,再加上懂得机关应用文的体例,了解本职工作的规律,掌握基层工作的情况和素材,写作应用文,就会得心应手。
我看了周保文的《山水有约》《溪山入画》的文章发表时间,周保文的很多游记,也是在其机关工作期间写的,特别是后期写的一些文化游记、文化散文,大多需要历史的钩沉、和相关门类的知识。
周保文在《与谁共舞》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散淡的文字就是我自适的家园。编织坚忍的枝叶遮挡风雨,搜集快乐的浆果喂养灵魂,钻取思想的火种点亮黑夜,采撷忘忧的花朵慰藉感情——在这里,凭借文字的提升,我业已达到了一种超越肉体的高度,在这样的高度上,我开始有幸蔑视我从前的奢望。”
著名评论家丁木先生这样评价周保文的游记式散文:“他选择了在行走与讲述之间展开他的人生画卷,在山川叶脉上寻觅梦痕,追寻文明;在行走中体验异域,认知世界,给心灵寻找一个在毫无拘束中裸露的契机。在同大自然亲切接触中学会以物观物,使描写对象自然呈现,也有直抒胸臆的写照,穿越心灵与现实,走向人文精神的高地。”
还有《我行我述》,应该是周保文中年以后的文章。那会周保文应该是担任梨树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或者是由副部长向文联主席过渡期。人过中年,我们经历过太多的风风雨雨,洞察了太多的人世变迁。尤其周保文,继承了其父亲周俭的性格——谦虚,我从没听讲过周保文高声调说话,我从没见过周保文鼓一下豹眼。周保文因为谦虚,不得不把内心世界藏在肉皮子底下,因为谦虚又不得不把自身苦闷藏进旅行的脚印。面对现实和挫折,苦闷、郁结、不快、失落常常缠绕心中。每当这时,文字就是医治创伤的良药。
这从他《我行我述》自序中我们多少能看出周保文内心的郁结和失落:“‘生命本身并没有意义,关键是,我们要赋予它怎样的意义。’已经记不清这是谁的至理名言了,然而我对此却是深信不疑。社会是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因此人们叫它‘大千世界’;生命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所以人们叫它‘芸芸众生’。由此看来,‘丰富’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常态,‘差异’是生命演绎和展开的必然。那么,构成人类生态这种丰富与差异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当然离不开生存的环境,当然离不开发展的基础,然而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恐怕还是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不同理解与追求吧?在现实中,我从来不对别人的生活方式妄加评论,但同时也决不对自己内心的那份执着妄自菲薄。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在宽宥一切人生取向的同时,也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既定的理想与抉择。我行走,我讲述——这当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但我又不能不郑重地声明:正是它们,构成了我对于人生意义、生命快乐最为现实的理解和把握。赋予生命以意义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不懈努力与追求的过程,而努力和追求从来都不是什么轻松的字眼儿,当我从工作的忙碌、生活的奔波、琐事的缠绕、怠惰的袭扰中艰难地俯下身来,一一写下这32个题目、顺次完成了这20万字的讲述时,其间1460个昼夜就那么急如星火般从我的眼前飞掠而过了。我从没奢望这些稚拙的文字会产生什么所谓的影响,但我坚信,再拙的文字也会让生命的行踪留下些许的痕迹。一个不知道黑夜的人,怎么能够奢望他去理解什么叫做白昼?一个不懂得死亡的人,怎么能够幻想他让生命的礼花绽放出应有的绚丽?我欣赏这样的表达:‘我思故我在。’但仔细想,思考真的就是证明我们存在的唯一方式了吗?当然不是。还是那句老话:‘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如有一千个生命,就会有一千种对于人生的不同演绎与诠释!那么你又选择了怎样的方式去展开自己人生的画卷呢?我常常这样反躬自问。回答是肯定的——我行走,我快乐;我讲述,我充实!”
周保文的这一段自序,我没有给分段,千字文章,一气呵成,甚至都没用“清清嗓子”或者“亮一下相”就直捣胸臆。这大概是周保文别样的狂,也可能只有在文字表述才会让他敢于这么铺张胸中的“存在”感。
我不知道周保文的郁结是什么。官场?不像,曾经的机会,要他去一个比文联显赫的衙门口他自己拒绝了。商场?不是,在周保文的人生履历中,我从没听到过与“钱”有关的只言片语。所以,以我世俗的眼界去寻找周保文的“郁结”,很难捕捉。那么,只能从他的文章里去寻找了,找来找去,终于捕捉到了些许信息,周保文的郁结,来自精神上的出口郁结。他热爱,却表述艰难;他自由,却行走蹒跚;他感恩,却无以着落。
其实,每个追求精神生命者,都存在这种不畅。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海子“水也不在温暖”。周保文也不例外,生命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生物学意义的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精神的张扬、激情的绽放。而一切由衷的选择、坦白的张扬、率真的绽放,归根结底,又都有一个深层次的动因叫“热爱”。为了热爱而不舍,为了热爱而倾注,为了热爱而忘我,为了热爱而守望,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而又无怨无悔的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地。
周保文这样解释热爱:“对于我个人而言,这种热爱成熟于高中,坚定于大学。1982年,我迎来了人生命运中一次最根本性的转折——这一年我以高于我期望的成绩考取了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尽管这不是我报考的首选,尽管我以优异的成绩入围了我的第一志愿——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但命运的笔锋还是轻轻地一转,让我幸运地走进了汉语言文学的殿堂。从此,大学学中文,工作教作文,改行写公文,业余工散文,日积月累,文字就成了深深地扎进生命核心的根。喜悦时文字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愁苦时文字会拧出伤心的泪水,疲惫时文字是精神的驿站,寂寞时文字是心灵的憩园。相守累积成了热爱,热爱反过来又坚定了守望。就这样一路行走一路书写,守着一树又一树不曾开花的文字,过着一个又一个清苦而又充实的日子。”
做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发乎天性,近于理想,顺其自然,这就是周保文心目中的自由。生性喜静,不慕繁华,耽于幽思,远避喧嚣,这是周保文性格的主调。可他又不甘桎梏于现实,羁身心于非愿,于是便只能疏离人事,亲近自然,游目于山崖水畔,寄情于文字之间。择机,就天南地北地乱走;得暇,便海阔天空地玄想。行走幽思之际,现实远去,欢喜顿生,人沐春风,心润好雨,不知不觉间灵魂的腋下便扇动起一双叫做快乐的翅膀。
周保文这样解释自由:“将足迹与幽思、快乐与自由诉诸文字,以此留住昨天,愉悦今天,照耀明天,这也是我关于旅行的文字为什么会占到全部写作内容的五分之三的真正原因了。‘不自由,毋宁死。’可见自由在生命中的分量有多重。通过文字的书写与宣泄,表达出人生的理想与愿望,这本身不就是我们生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吗?”
对于每个个体而言,热爱固然是重要的,自由固然是重要的,但仅仅是一己之私的热爱与自由,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有感恩与担当,还有义务与责任。
周保文这样解释感恩:“出生黑土地,大地上的万物生灵父老乡亲养育,父母的殷殷教诲,大学四载,饶有恩师,耳提面命。参加工作之后,更是长者指点,同事切磋,积之既久,收获颇丰。尤其当自己辛苦而成的文字见诸报端,熟悉和陌生的朋友们一再地关注着、鼓励着。这一切,在一个本来敏感的内心里,怎能不汹涌起一种叫做‘感动’的波澜呢?然而,‘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憔悴半生,努力经年,除了一篇篇并不成熟的文字,还有什么可以回报那些值得我们感恩的人们呢?于是,索性将自己学习的心得、曾经的脚步、思考的点滴、感情的絮语,精心地编织在一起,一股脑儿呈献在大家的面前。哪怕这些文字只是一次旅行的向导,一个景点的指南,一个温馨的贴士,一个实用的攻略,总之只要对得之者稍有裨益,那我已经是万分地欣幸了。”
周保文热爱梨树这片黑土地,热爱文字;周保文追求在黑土大地上自由生长,在文字王国里任由翱翔;周保文感恩黑土地上的万物生灵,感恩文字让他畅抒所想。
周保文是黑土大地培就的根,有文字的脚印铸就的魂。无论是彷徨、苦闷,都是精神世界再上一个层面的痛苦挣扎。